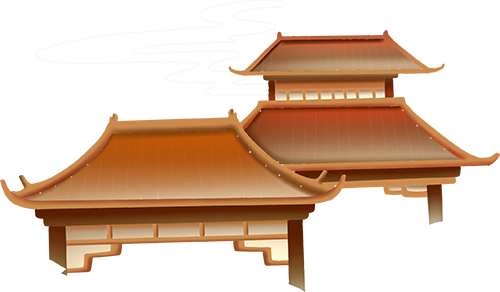中国人平均每天只需工作3.5小时……你被平均了吗?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叁零柒计划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分析或评论, 统计数据或调查报告
关键词:小时, 平均, 劳动关系, 时间, 朋友, 生活, 摸鱼
涉及行业:
涉及职业:
地点: 无
相关议题:工作时间
- 中国居民在有酬劳动领域的平均工作时间为每日3小时27分钟,但实际参与有酬劳动的人每日工作时间为6小时23分钟。
- 不少劳动者面临的实际工作时间远超标准工作制,加班成为常态,打乱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 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仍需应对工作任务,如接听工作电话或处理紧急任务,影响了正常的休息和生活。
- 工作中存在的管理问题和不合理要求,如对人而非对事的负责,以及过度的工作量,加剧了劳动者的压力和不满。
- 劳动者在面对工作压力和时间管理上的挑战时,感到自己的自由时间和个人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编者按
2024年10月底,一份名为“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的统计数据横空出世,所谓有酬劳动领域,居民每日平均时间为3小时27分钟。这个抓人眼球的数据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呢?首先是假设所有人都有双休,将休息日纳入分母,其次是对所有调查对象进行平均(实际参与率仅为54.1%),最后是将6-14周岁几乎不可能参与有酬劳动的人纳入分母(这拉低了参与率)
统计者大方地给出了参与者的每日有酬劳动平均时间,6小时23分钟,即每周44小时41分钟——虽然挤掉了一些水分,但是这仍然是在假设每周工作五天之后加权平均得到,但显然的是,不少劳动者实际上无法做到每周五天工作日。具体的参与者每项活动的平均时间如下:
或许有时略显滑稽,但是在互联网的舆论声浪中,我们依然时不时能够听到针对要不要落实(早已写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八小时工作制”的争论。但归根结底,统计数据终究只是苍白的背景板。每个具体的人的生活,往往都游离在这些冷酷的统计数字之外。扪心自问,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令人满意的吗?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忙些什么?还有多少能够自由支配,用于自由发展的时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期望的工作又是怎样的?
针对这些问题,许多读者朋友们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与做法。我们决定将这些内容整理出来,分享给更多读者朋友。
“‘偶尔加班’完全打乱了我工作与生活的分界线”
在回答“工作时间”到底有多长之前,我们似乎不得先不回答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算是“工作时间”?对许多人来说,在“上班”与“下班”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限,似乎并不容易:
我最晚在凌晨三点接到过导师发来的工作信息,和在晚上十一点四十接到过导师打来的工作电话。身边也有朋友在饭点、夜间、病假状态、年假状态中接到工作电话,甚至直接开启线上会议。
——乙己
我最近的一次实习是在一家国企,写明的工作时间是非常标准的朝九晚五,但是它的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非常模糊,一旦领导有任务需要你完成,即便是下班时间或者周末,即便是在地铁上抑或是出去吃饭逛街,都需要你以很快的速度响应工作。
——高川
在教培这个行业工作,我需要备课。因此晚上时常被“锁”在床上一样,眼前只有手机屏幕、川流不停的网络信息,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手指更是机械分离地在划屏幕。这种“预备工作”的状态,每天大概又要4小时。
——岁月静好
客观来说,工作占用周末的总时长并不多,但好好的一个休息日很容易被工作渗透成了筛子,应有的休息其实并未到位。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我的工作是领导安排的,我无法比较有计划地支配自己的时间,除非是真的没时间,否则我无法推迟或者拒绝掉一项工作。
——山火
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生活与工作的分界线被各种所谓的“偶尔加班”搅和成了一通浆糊:
“偶尔加班”完全打乱了我的工作与生活的分界线,我必须承认我的可支配时间是互相挂了线的风筝,线的另一头是同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绕进去的倒霉蛋。
——蓝色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还有力气“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吗?许多朋友也分享了自己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在休闲娱乐等等方面的变化:
和朋友一起出去玩都只能选在周边,因为每日2h的通勤已经消耗了太多体力。我只想在床上躺着,一直躺着,再多就是看点综艺或搞笑视频——整个人就像行尸走肉。活力也好,喜悦也好,那些曾属于我的好东西,都已经被抽空了。
——白山
相对自由的时间是每晚20:45开始至当日00:00,共3小时15分钟。但是(这里面)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是在成瘾性地使用手机,成瘾性地刷视频类APP上的视频。
——莫哈维
工作之后就明显觉得不一样了,一个明显的指标是,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我的工作还不算特别卷,只是普通的办公室工作。但是,看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时间却没有减少,甚至还上升了,我想,工作其实制造出了更多碎片时间,那种让我无法静心认真去做点什么的时间。现在下班后只想看着B站吃一顿丰盛的外卖,安抚自己因打工而受伤的灵魂。
——旺角金鱼
这种碎片化的任务一旦侵入你的非工作时间内就非常可怕,你很难在非工作时间内开展任何长时间的专注的活动,抑或是获得很充分、很深度的休息,时不时的碎片化工作让你很难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你需要每时每刻保持紧绷,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这种工作模式也让人很难去户外进行一些休闲的活动,因为你还是要尽可能地在每时每刻都保持一种可以工作的状态。
——高川
事实上,也有伙伴分享了自己的挣扎:
我拒绝接受自己的可用时间只剩每晚的几个小时。我强制要求自己,必须在可用的时间里做“有意义的思想活动”,最终我什么有意义的思想活动都没做成。它最后离奇地变成了一套打扫、整理屋子的强制性流程,再后来就是强迫症。强迫思维、强迫行为自此如水银泻地般侵袭了我的生活与行为,也包括思维的方方面面。我现在可以说是一方面勉力维持着完成工作的同时,以免在日常生活的瓦砾上重建生活。
——莫哈维
“我曾患有微信恐惧症”
在上班期间,大家在忙什么呢?许多有过制造业流水线工作经验的朋友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总体而言,工作强度极大,“机器不停,人就不能停”。另一位朋友也提到,产线上的工作即便单调乏味,但“确确实实是需要有人或者机器去干的事”:
我在一家纺织厂待过两周,那是我第一次见识流水线的恐怖。早上七点半就要到厂点名,一直干到十二点,下午班十四点半到十八点半,晚上半强制加班从十九点半到二十一点半(不加班的话一般就把你开了)。只有周六可以休一天。机器不停,人就不能停。
——水
2010年5月至2016年6月期间,我基本都是在做产线员工,工作基本都比较基础,实实在在的拧螺丝和组装,打包,虽然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但确确实实是需要有人或者机器去干的事,无聊但必须要做。
——丸子
流水线上的世界往往单调,枯燥,摧残人的身心。而所谓“白领工作”的疲惫则是另一种形状——老板派下的工作像“一堆精准控制重量的鸡毛”,上级奇怪的脑回路让人无所适从,看似更高效省心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同样会让人心力交瘁。到最后,我们甚至会对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产生迷茫:
老板总会在我快要把手头上的事完成之际,派下更多的工作,永远也做不完,但也不是都急着要,就像一堆精准控制重量的鸡毛,不至于把我压死,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白山
有一次我和上级开会,他问起业务细节,我简略地做了回复。之后发生了如下对话:
上级:为什么说的这么简单?
我:因为实际上逻辑并不难。
上级:我不相信。
我:那我可以把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请过来开会我们详细地了解一下。
上级:什么事都要技术部门的人来介绍那我要你做什么?
这番莫名其妙的对话给了我非常大的冲击,我开始意识到不能这样下去,我应当对我自己的工作流程有发言权。
——扬慈
OA系统相信是许多打工人的噩梦。几乎一切东西,比如请假、采购,都要在里面“走流程”:填写一个表格,经过层层审批,多部门签字,最后批复。它所需要的时间和繁琐,和它的重要程度是如此地不匹配,是一项十足的“狗屁工作”。
——旺角金鱼
我在工作里投入时间和精力时,其实真的会认真投入出于责任心避免把事情搞砸,但当我完成一个个紧迫的任务,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也无法用公司的价值和利益来替代心里的那个空位。“职业发展,更好的平台”是我难以理解的概念,所以在我眼里是空洞的。
——东
正如许多朋友提到,“最痛苦的事情是,我不是对事负责,而是对人负责":
我现在的工作其实挺理想的,只有一点不太好,我不是对工作本身负责,而是对领导负责。唯上不唯下,唯权不唯实。
——水
在公司里,最痛苦的事情是,我不是对事负责,而是对人负责。老板心血来潮想整活儿,我就得加班了;同事被优化,我的工作量就翻倍了。我只想踏踏实实做好我份内的工作,认真负责,走在ddl前面,但这似乎成为一种奢望。
——白山
大家都知道衡量一项业务的表现可以用很多种衡量手段指标,对于某些领导来说,这些指标数据也需要小心翼翼地去呈现。指标不能太差,太差的话会被领导逼问:干的这么差是怎么回事?但是其实也不能太好,因为一旦指标太好,在领导眼里这个指标就变成了没有说服力的指标。有时感觉高层的汇报像是在过家家,一字一句都需要斟酌谁看到会不会不开心,会不会授人以柄。一线基层员工拿着最低的工资,在报告上逐字逐句修改,修改的报告成了高层会议上高层各自的弹药——而这些和一线员工究竟过得怎么样几乎毫无关联。
——扬慈
另一些工作则需要面对更多的不可控制的人与事:
比较难搞的是,教培这个行业,你遇到的学生各色各样,付出的情感劳动也会相应波动。如果接到一个攻击性很强/厌学到极致的学生,ta的每堂课都需要我课后报复性熬夜来恢复。
——岁月静好
我目前是在某大城市的高校做外包的图书馆管理员。图书馆的出入需要刷卡,可是闸机通常都非常非常灵敏得不正常,因为有学生就是带个耳机电脑都会发出警报声,我作为管理员不得不询问有没有借书啥的,确保不是书没有消磁。我本来想借着清闲的职位来学习,可这样的每天长达12个小时的过程中,我无数次地被警报声夺走注意力,可还好我的工作是上一休一,导致我格外珍惜自己不上班日子,因为可以完全完全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川木
我曾患有微信恐惧症,只要微信一响,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很紧张,甚至要做好心理准备才能点开。我们是做工程的,微信一响要么是领导找你,要么是其他同事或者业主找你,还有最糟糕的情况-现场出问题了,毫不夸张的说微信运动步数的提示音会让我感到害怕。我也曾试图将生活与工作分开,学习前辈们工作一个手机号,平常一个手机号,然而,当我切换到日常微信的时候会非常担心在工作微信错过消息,反而更加提心吊胆,最后又切回来了。
——蓝色
即便不谈工作内容,上下班通勤往往都能让人在一瞬间崩溃:
那时每天为了通勤,7点起床上班要花一个小时打车,下班要花一个小时打车,一次70,一天140元,还被卡了报销。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更换了住宿地。一次,夜晚8点钟下班,坐车回住宿地时,在车上突然很难受,那时候就想“我给司机师傅70呢,我干活的钱全给她赚了,我在她车上哭了不是吐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但当时自己大男子主义作祟,想着不能在女师傅面前哭泣,就忍住了,到了寝室,室友又都在,也不好意思哭,最后到底是没哭出来。
——蓝色
“随着工作日久,我也有了更多摸鱼技巧”
工作有那么多不如人意之处,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学会摸鱼。事实上,许多朋友往往一开始带着满腔热情努力奋斗,最后却往往发现,勤奋的代价往往是让自己受伤。于是,大家开始学会卡ddl,利用“碎片时间”,或者总结出一些“让自己更轻松”的工作方法:
我需要把本来很快很简单的工作弄得拖拉又复杂,让领导觉得我是在认真工作。有时候我会负责稿件撰写和视频剪辑的工作。一开始我是很快就上交了,但要求也越来越离谱。和公司定运量指标一样,今年9500万吨,明年就敢1亿吨。之后我就养成了卡在deadline之前再完成的习惯。
——水
我只要完成了当天分配给我的进度,并在不算很晚的时间上交,就还能过得去。所谓“不算很晚的时间”,意味着我其实可以故意拖延一下,摸一会鱼。不过一旦工位本身处于一个暴露视点,即使能摸鱼,也无法实质上开展其他活动,所以摸鱼抵不了下班。
——乙己
随着工作日久,我也有了更多摸鱼技巧,比如延长工作时间内的用餐时间:早饭班上吃,午饭吃完溜溜弯;比如用碎片时间预约医生、餐馆、安排出行;比如深度使用微信读书和小宇宙——播客真是通勤利器!
——旺角金鱼
由于课程抽查主要看学生老师有无违纪行为,而家长和学生也是想学到知识即可,所以可以自己出一些资料来用,在这一点上不必担心被公司追责。这样能给自己喘息的机会,毕竟研发题目都是有精力的时候提前做,而一次研发可以用好多次,班课、一对一,带多少学生就能复利多少次。第一次教的时候,一般还把握不准,所以可以在基础比较好的一对一学生/人数较少的班课那里试水,再进行改进。不然第一次就要求自己做出适合各个水准学生的材料,在心理和时间上反而会进度缓慢。
——岁月静好
另一位朋友更系统地谈了一下这个问题:摸鱼是必要的,但是核心在于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真正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换句话说:“要先爆破掉对岗位任务的天生的责任感。”毕竟在许多情况下,你做得越多,“轻则浪费自己生命慢性自杀,重则反而对社会和他人有害”:
我会区分“指派任务工作时间”和“自我安排工作时间”。前者用来完成岗位中上级指派的任务,后者则是在完成指派工作的基础上,会主动额外承担一些任务。
对于指派任务工作,我的策略就是尽量提高效率、减少时间浪费,把实质上花在这些工作上的精力降到最低。这不一定是一口气把这些活干完,也可以交替着摸鱼或干有意义的事情,把一个工作日“撑满”。
对于额外工作,依然是“政治挂帅”。在这里,要先爆破掉对岗位任务的天生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本质上是工作伦理的变体,我也曾在上面饱吃苦头。换言之,先想清楚自己岗位的这份工作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如果你认可,那么再去考虑投入更多的时间把这件事儿做好;如果不是这样,那不妨放弃掉这份部分工作。对于无明显意义的工作,那么拼命干啥?你做得越多,轻则浪费自己生命慢性自杀,重则反而对社会和他人有害。
那对于个人成长类的额外工作,我认为也要祛魅:都是额外时间了,为什么一定要“工作”而不是“闲暇”呢?这部分时间更多应该理解为有真正“自由活动”的时间。
——大目
关于工作,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那么说到底,大家心目中的好工作到底是怎样的呢?许多朋友指出,理想的工作一定要做到清晰地区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双休,日常八小时可以累点,但是八小时后能将生活与工作分开。我有时候会想,能不能三年换一次工作?将未来30年分成十份,尝试十次能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呢?
——蓝色
或许对我来说,相比于工作时间的长度,能够安排好工作时间,才是对我的工作成长更有帮助的。
——山火
所以我理想中的工作其实就是一周五天,然后每天八小时,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十分清晰的工作。在工作时间内你可以非常专注地投入工作,然后在非工作时间内,在下班之后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必为任何工作中的事情而烦恼,享受深度、充分的闲暇时光,支配属于自己的时间。
——高川
我对于下班后是否能拥有自己的时间这件事一直感到焦虑。我希望能把时间利用起来,希望有一份“工作之外的事业”。我希望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能维持下去,即使等到自己三十多岁以后在基层岗位面临和年轻人的竞争压力,即使公司要裁员。
——东
如果让我们的父母辈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很可能会觉得好的工作就是“稳定”的工作。然而,“稳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正如一些朋友提到的,事实上,谈及稳定时,我们想要的其实是一种保障——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有尊严,坦然地生活:
理想工作是不影响接送孩子上下学,可以干到退休,可以准时下班,下班后线上工作不要太多,工资除了开销,攒下十年的钱可以买的起县城的一百平以内的房子,退休后可以拿养老金。
——丸子
在法律体系中,“劳动”永远与“社会保障”相伴相生。大部分人看似在追求“稳定”,其实想要的更是一种“保障”:我们不必然抱着一个铁饭碗干一辈子,但只要勤勤恳恳地付出,在遇到大事小事、各种变化乃至困境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有尊严地、坦然地生活。
——白山
最后,也有一些伙伴提到工作本身能够带来的各类价值。有的朋友希望工作与自己的兴趣挂钩,也有的朋友则谈到,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帮助自己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或许在今天的许多人眼中,这个目标似乎有些遥远,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坚定这样的目标,我们才不至于在雇佣劳动关系内部彻底迷失:
我理想中的工作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具体到我个人可能是,“白天做翻译,晚上和周末做家教,有空时做自媒体。”
——白山
当前社会背景下的理想工作,或者是我认可其中的意义,为此我可以平衡好指派任务时间和自我安排时间的比例,在工作中多实现社会价值和提升个人能力;或者是这份工作指派任务相对简单且没有太多危害性,我可以利用闲暇做些创造性的活动。
——大目
理想的工作可能可以让我实现三个目标:不给作恶的审查机器效力;能够让我养活自己;能给自己想要推动的事业尽一份力。对于工作本身,首先是要能够提供基本保障,遵守8小时劳动制。通勤时间的话,那除非我搬到基础设施对普通人更友好的国家了。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只能导致这种惨痛的通勤时间。另外,我希望工作场所能够贯彻性别平等原则,尊重、保护LGBTQ+人士。
——莫哈维
结语:告别无奈,劳动还可以是幸福吗?
当“牛马”们能够暂时卸下缰绳,转头检视自己的时间分配,往往也只能感到怅惘和无奈。工作彻底塑造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它的影响远超“八小时”。处在雇佣劳动关系内部的我们,尽管仍然怀揣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往往只被淹没在过劳与匮乏的浪潮起伏间。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疲惫、焦虑和失落,不仅是个体的危机,更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整体危机在它每一块燃料身上的映照。当这种危机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它也终将不能再维系它自身。
在怀揣许多痛苦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忘记对未来的渴望。它是更有意义的工作内容,是更公平的劳动时间分配,是更可靠的劳动保障,是超越利润至上、领导至上的工作模式。更有雄心地说,雇佣劳动使劳动伴随着痛苦,而使不劳动成为一种幸福,那么我们能否“把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追寻一种幸福的劳动?本文写作者和读者们的困境,并不是我们作为“牛马”的先天命运,而是具体的社会制度塑造的结果。正视这一点,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是我们期待的劳动关系;为了到达那样的目标,今天的人们要怎样行动。
END
投稿
自由投稿|[email protected]
访谈问卷|可扫码填写问卷
精彩锐评|若留言不可见,为系统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