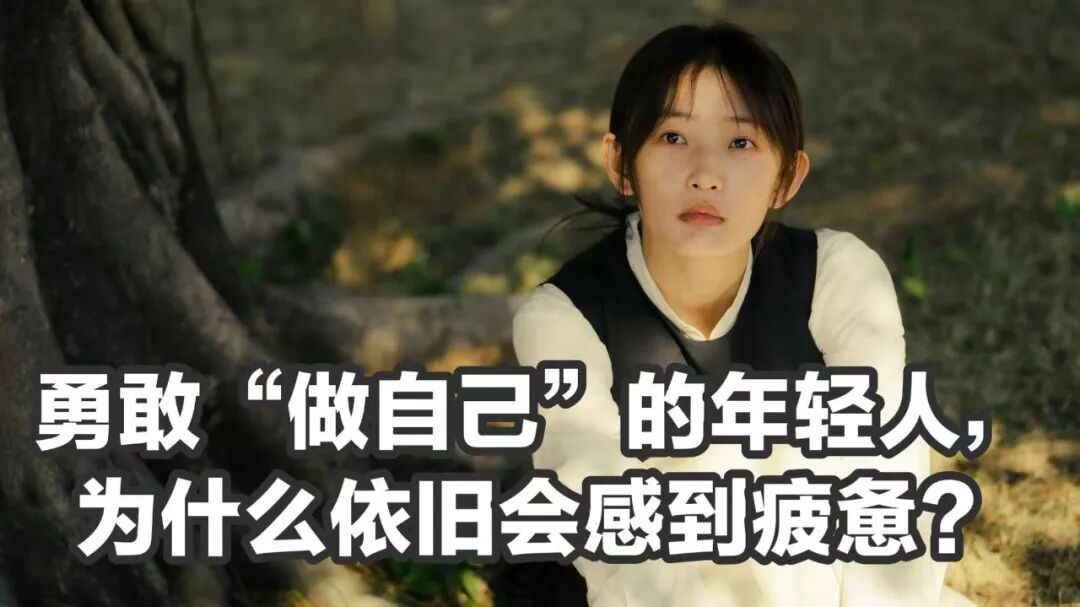光鲜想象背后:“难以脱身”的底层女主播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主播, 直播, 公司, 运营, 直播间, 内容
涉及行业:体育休闲/文化娱乐, 服务业
涉及职业:白领受雇者
地点: 无
相关议题:工人仲裁/起诉, 工资报酬, 灵活就业/零工经济/平台劳动, 劳动合同, 就业
- 许多底层女主播在签约时未仔细阅读合同,合同中常含有高额违约金和对主播单方面约束的“霸王条款”,而公司义务则模糊或未明确写明。
- 主播与直播公司签订的多为经纪或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司法实践中多将其认定为民事合同关系,主播违约时需承担合同约定的责任。
- 直播公司常以未完成直播时长、主动解约等理由起诉主播,主播因缺乏法律意识和证据,败诉概率高达90%。
- 公司运营人员可随意调整主播的直播内容和时长统计,主播实际工作内容与招聘承诺不符,且工资、资源支持等承诺难以兑现。
- 直播行业门槛低但实际要求高,底层女主播多因对行业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而入行,最终陷入难以脱身的合同和劳动权益困境。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湖南华专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炎从2018年开始代理直播相关的诉讼案件,他发现被起诉的很多都是最底层的主播,女性的比例为80%-90%,其中20-28岁的女性居多。她们抱着成名和对直播业的光鲜想象进入行业,却发现等待她们的是一个难以脱身的处境。
埋坑的合约
2023年8月,如果不是一条来自法院的短信,林玥已经淡忘了上一段在直播公司的经历。
短信显示,她被前东家——安徽合肥的一家直播公司起诉,对方向她索赔20万。当时,距离她离开那家公司已近一年。她立刻给法院打电话,确认是真的后,吓得浑身发抖,大哭。她负担不起这笔违约金——正在做外贸业务员的她,一个月只有5000元,“每个月都花光”。
林玥26岁,长着鹅蛋脸,杏仁眼,皮肤很白。身材不算瘦,常穿紧身、糖果色系的衣服,衬托出玲珑的曲线,给人一种可爱和成熟兼而有之的美感。她告诉本刊,自己2022年入职上家公司,应聘的是服装拍摄模特,岗位招聘信息上注明了“高薪+住宿”。面试时,工作人员对她说,摄影师是从杭州请来的,有丰富的拍摄经验,能够把她包装成“网红”博主,但这个岗位需要配合直播一起做,每天播四五个小时。
公司看上去很正规,是一座大厦中的一层,干净整洁,工作人员有十多个,运营很热情。直播室有四五间,很敞亮,室内有很大的玻璃窗,放着一台电脑、手机支架、麦克风和发箍等。工作人员拿出合同让她签个字,她看到合同的名称是“经纪合同”,上面规定了每月的直播天数和时长。林玥没有仔细看那份合同,但看到20万的违约金时也觉得不合理。不过工作人员解释说,“没事的,你放心,只是走个流程。”
《燃罪》剧照
进入公司后,林玥发现工作跟她想象的有些不一样,跟服装模特几乎没有关系,主要业务是维护“榜一大哥”,让大哥掏钱刷礼物。断断续续直播了十几天,林玥觉得运营只想挣快钱,不会教她直播。拿了3000块钱工资后,她就没再去上班。运营断断续续地问过她几次“什么时候能回去直播”,林玥都没有搭理,“我当时一方面觉得他们是骗子公司,一方面是逃避心态”。现在回想这个过程,林玥觉得自己太没有法律意识,“感觉(签合同)像过家家一样,签了也没啥事。觉得不想播了,不播就行。”
安然也是在进入深圳一家公司后,觉得自己受骗了。她和好友唐悠悠应聘的是团播主播。这本来应该是一份以跳舞和PK(两位或多位主播在直播间进行的一种互动竞赛形式)为主的工作,但签合同时,工作人员对她们说,由于团播是面向海外的,公司的网络不好,PK经常中断,所以暂时无法开播。她们外形条件很好,可以两个人一起做双人直播——公司出脚本,她们出镜表演。等之后网络好了,再转团播。公司向她们许诺了每个月12000元的保底和1500元的房补。对于学历不高,工作没多久的两人来说,条件充满诱惑。
但实际的双人直播没有脚本,只是聊天。运营很在意页面标题,经常提醒她们写上“xx品级私教”,“宝安私教+飞机符号+可”,实际是暗示擦边。运营说,“别人问什么都不要回,等刷飞机礼物就行,谁刷飞机就意味着可以加主播微信。但是有(被封号)风险,你们不要乱说话。”但账号仍然很快被封禁。也因此,两人完不成合同规定的每月直播156小时的直播时长。运营以此为由没有给她们发放当月的保底工资。7月之后,账号又因为“擦边”被封了几次,“从5月22日开播到现在,没有拿到一分钱。”
受访者供图
她们去找运营,对方回应,“如果你们有任何争议,按合同走”。安然这才仔细看当时签的合约,“里面埋了很多隐形的坑。”比如“乙方保证按照双方约定完成直播时长。直播应为有效播出,严禁故意挂机行为。乙方完全认可甲方关于时长的统计数据,甲方有权对乙方的直播时间进行调整以保证直播效果,乙方应当给予配合。”这意味着,运营有权随便更改她们的直播内容和风格,而且,如果公司不承认她们播的是有效时长,“就算白播”。再比如“就所有因乙方违反或未履行本协议所有的乙方承诺、保证及义务,或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微信,QQ等社交软件同意无效)单方解除本合同的,均视为违约。”
吸引力法则
凉子是一家mcn机构的经纪负责人,她告诉本刊,权利和义务不平等的条约在直播界是普遍的,不单是主播,博主、艺人的合约也是如此。“公司培养一个主播、博主或艺人,需要3-5年的长期投入,这期间,公司会在他们身上投放很多资源,比如直播的设备、前期的投流、内容的策划,还有运营团队。到后期如果主播不续约,对公司来说很亏。所以一般公司都会用很多条约来约束主播。”她说,平台公司和主播一般签的是合作协议、经纪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是因为主播的收入主要来自打赏,难以在劳务合同中界定。
即使如此,在凉子看来,林玥和安然签订的合同都是有问题的——没有写明甲方(平台)所需要承担的义务和法律后果,列出的公司应给出的资源扶植也不够具体,更多是对乙方的约束和违约责任的要求,“其实属于‘霸王条款’”。凉子说,正规的公司允许主播增加或删除合同中不合理的内容。
《绝世网红》剧照
湖南华专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炎从2018年开始代理直播相关的诉讼案件,到现在接触了上千名主播。李炎告诉本刊,直播行业的爆发式发展已经有十年左右,这几年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加,网络直播行业的“坑”逐渐透明化,因此他接触到很多主播会在签合约之前先问律师的建议,当发现合约的义务很重时,部分主播会选择不签。在李炎看来,那些选择签约的主播有70%-80%是因为对行业和自己抱有过高的期望,对合约的风险视而不见或认为其在可控范围内,只有小部分是因为年龄太小、文化程度太低或第一次进入行业,判断力较弱。
李炎接触的主播被起诉类案件,被起诉的都是最底层的主播,女性占百分之八九十,其中20-28岁的女性占多数。常见的理由包括未完成约定的直播任务,主动提出解约,合同期内在其他平台直播等。李炎说,被起诉的女生,要么刚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要么找不到理想的轻松的工作,她们往往对直播行业怀有光鲜亮丽的想象,想成名、赚大钱,又都容易轻信别人,法律意识淡薄。凉子说,娱乐主播行业对很多想入行的人来说像一个“梦工厂”——行业的热闹带给大家错觉,似乎人人都能做主播。
《人生开门红》剧照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4-2025)》的数据,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经营网络直播业务的新媒体公司13841家,全年新批3828家。至2025年5月,主播帐号累计开通1.93亿个,月活跃开播帐号3326.7万个。凉子说,注册直播公司和成为主播的门槛几乎为0,“现在几个人搭一个团队就能注册一家公司。只要有手机,会打开摄像头就能成为主播。”
但事实上,凉子告诉本刊,主播是一份门槛很高的工作,“如果去看那些出类拔萃的主播,会发现要做好主播,不能只依靠展示颜值和才艺,幕后要研究内容如何产生吸引力,也要做客户关系的维护,也就是所谓对榜一‘大哥’‘大姐’的维护,就像传统的销售一样,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还要看个人的素养、个性,以及运气。”
而且,2023年之后,直播行业流量严重下滑,机构的生存并不容易。一位直播机构资深从业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相比从前“70%自然流量+30%付费流量”的组合,2023年直播间的自然流量占比不足20%。李炎说,很多直播公司开始靠起诉主播获得赔偿来挣钱,一些法律咨询公司甚至推出起诉主播的套餐,教直播公司以很低的代价起诉主播。这些直播公司会在签约主播时广撒网,赌她们无法坚持完成协议内容,等主播违约就起诉,有些直播公司,每年起诉主播上千起。在凉子看来,一些公司通过大量签约主播不能获得营收,自然而然就要缩减成本,起诉主播是收回过去投入成本的一种方式。
根据李炎的经验,一旦被起诉,主播败诉的概率达到90%。她们通常没留存企业存在过错的证据,比如公司诱导签约,没有解释合同风险,或者存在不发放工资,要求主播去播“擦边”低俗的内容等违约行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侯海军从2018年开始关注网络主播群体的劳动权益保护,他告诉本刊,判断主播是否应当向直播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关键在于双方之间的合同、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法律效力。如果属于劳动合同,主播与公司的关系被认定为劳动关系,败诉的多数是公司。但司法实践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法学学术和司法界主流观点,不认同新媒体公司与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构成劳动关系。如果双方的法律关系归于民事关系,会由民法典按照民事合同来对待:遵循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原则,主播自愿签约的,要按照合同内容来履行;达不到合同中哪怕是苛刻条款的,也要承担违约责任。
直播的女孩
安然做直播不算偶然。2017年到2020年初,她还在上中专时,曾经兼职当过烘焙店的学徒、做过服务员、健身教练、招生老师、行政、主持人,“每个行业都想尝试一下。”但这些工作不是太累,就是工资太低,没有她想长久留下从事的职业。
19岁中专毕业后,安然开始在哥哥的数码工作室做短视频博主。工作室开在深圳华强北,主要的业务是卖二手手机,她的主要工作是拍摄短视频,教大家如何避坑挑手机。她们也会定期直播,粉丝可以通过直播间和橱窗下单,也可以留言喜欢的机型。她觉得那是个短视频的红利时代,她的每一条视频都火了,点赞量最高超过千万,账号积累了30多万粉丝,“赚钱很快,一天能卖出去几十台手机,一台手机的价格在2000-5000元。”
《猎罪图鉴》剧照
后来由于政策的原因,这门生意无法持续。她随后又换了几份工作,都和直播有关系。在来到深圳的这家公司之前,安然的上一份工作是团播。她回忆,团里一共有6个女孩,轮流上场跳舞。自己跳舞的时候,音乐不结束不能停,其他时间要在底下喊麦,发弹幕活跃气氛。她向本刊记者解释,一开始选择这份工作,因为自己“喜欢自由”,一赚钱就想“摆烂”,和闺蜜出去玩。这些工作热闹绚丽的场景,让她觉得自己距离能轻松赚钱、光鲜亮丽的“网红”很近。但实际做起来却完全不是想象那样。直播间少的时候有一两百人,多的时候有几千人。有时需要做PK,吸引粉丝,她会一左一右抱两个人,身后再背一个人,转圈、深蹲,经常摔,摔得腿上全是淤青。她干了三个月,因为太累,就不干了。
不管是团播工作还是后来的聊天直播,都要求主播在镜头前显露和展示自己的容貌和肢体。安然对这种展示已经习以为常。在她的理解里,这类工作的性质就是“靠自己的才艺和魅力去吸引人消费”。林玥也有类似的感觉。2020年,林玥刚毕业时也做过聊天主播。在她的记忆里,她经常跟人线上打PK,“大部分时候只要坐着,做扩胸运动,偶尔才做跑步、蹲起这类惩罚。一天都能挣几千块钱。”她说,“那时‘大哥’哐哐给你刷七八辆跑车,好多餐饮小老板,刷礼物可大方了。下播之后只要给他们发一条感谢的短信就可以,有的‘大哥’也会给我分享日常,比如在看哪部小说,我这里像是他的一处精神寄托。”
之所以进入现在的公司,安然看中的是两点,一是公司许诺的工资很高;二是她觉得团播现在很火,出圈的机会多。但开始工作后,她发现直播运营人员的要求有些变味。安然说,运营对她们妆造的要求是性感——必须要化全妆,贴假睫毛,做高颅顶,衣服要紧身、裸露。她们的妆造要经过运营的审核,不符合要求不允许开播,或被要求下播。因为穿低胸的衣服,安然的直播间被平台提示了好几回,运营让她拿一张纸巾夹在衣服里,遮住乳沟,但不能不穿低胸装。
《一念天堂》剧照
关于如何做聊天直播,运营曾经给她们发过一套类似的话术:看到一个人进来,在他观看的1-5分钟,主播要查“户口”,比如问,XX哥,你也是深圳的吗,你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的?目的是快速了解直播间观众的付费能力,把“大哥”找出来。第5-7分钟,目标是让潜在“大哥”关注自己,会问比如“XX哥,你觉得我好看吗,觉得好看能不能给我点个关注呢”类似的问题;再接下来就是要礼物,从小额的礼物开始要,循序渐进。
安然说,直播时,运营也会在直播间里观察,随后登录主播的账号,把那些不刷礼物、等级低的人拉黑。和安然同公司的一名主播,黑名单里有2000人。对于那些等级高、刷过礼物的人,运营会用主播的账号逐个私聊,让粉丝刷礼物,一个“飞机”是3000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300元。安然下播后,经常看到后台一片是“自己”私信过的账号。在这样的模式下,安然告诉本刊,她的直播间经常只有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不超过10个人,“人一多就会被举报”。那些刷了“飞机”,加了微信的“大哥”通常也都有特别明确的目的——约她见面。安然接触了十几个“大哥”,年龄在21-40岁不等,各行各业都有,比如学生、公务员、富二代。他们加微信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今天晚上出来,给你5000。”
《猎罪图鉴2》剧照
同为主播的李维告诉本刊,“擦边”的内容在短视频平台有不小的受众,容易获得流量,“就像把夜场搬到了线上。”李维说,一些平台规定不得展示色情内容,否则触发封禁。“擦边”内容能躲避封禁而“既让你感觉到性,又不触发封号”,而且通过营造虚拟亲密关系或者群体暧昧氛围能激发观众的情感投入和冲动消费。李维说,一些平台为了追求流量,只看弹幕和付费数据,并没有真正的关注直播内容,使得“擦边”内容有泛滥的趋势。一名主播告诉本刊,自己2022年入职江西的一家直播公司做兼职主播,几个月里,直播间只有四五个人,有时候没有人。她去别人的直播间学习经验,发现那些流水很高的主播,是在穿暴露的衣服,表情诱惑地跳扭腰扭胯的舞蹈时,直播间里的人才多起来,“一下子就来100多个”。
对于“擦边”的工作内容,本刊采访到的主播们起初都表示反感,但合同的制约让她们不敢轻易停播。然而在公司待的时间久了,运营的标准也在慢慢吞噬她们的感受。安然说,一开始在后台看到那些约不约的私信,她“都炸了”,后来看得多了,变得麻木。她渐渐觉得,这只是一份工作,目的是为了“薅大哥的羊毛”,运营怎么说她怎么做就行。有时流水不高,有的主播还会怀疑自己的长相和努力。安然说,她甚至开始习惯运营对她们的不尊重。运营对她和朋友的备注是小B和小F,对应着她们的罩杯。一开始安然说了很多次不要再这么叫她,最后她觉得“无所谓”,自己“不是开不起玩笑的人”。
《最佳利益》剧照
虽然迄今没有拿到一分钱,但在和公司运营“理论”之后,安然继续上播。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她与公司签了半年合约,运营告诉她,如果她离开,要赔付违约的钱和公司对她的投入成本。她决定把剩下的时间熬过去。
(除李炎、侯海军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排版:球球 / 审核:同同
招聘|撰稿人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未经许可,严禁复制、转载、篡改或再发布。
大家都在看
“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